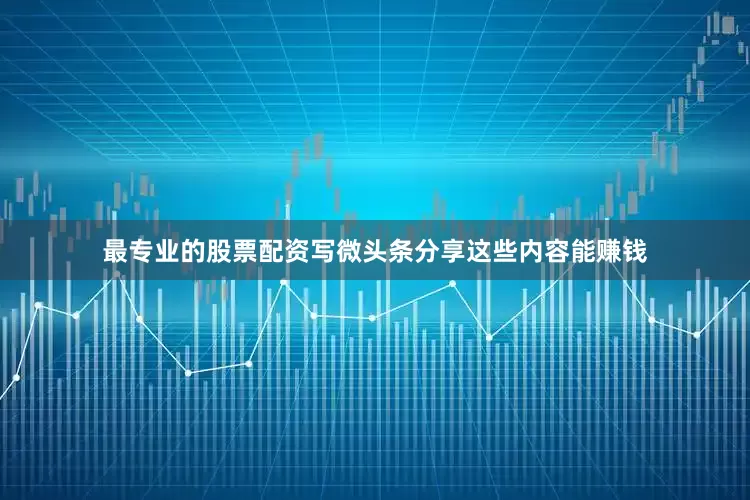公元749年秋,长安大慈恩寺。两位中年男子并肩登临大雁塔顶。西风卷起他们微霜的鬓发,眼前是万家灯火的长安城,身后是即将奔赴的万里边关。高适挥毫题壁:“万里不惜死,一朝得成功”;岑参含笑应和:“誓将挂冠去,觉道资无穷”。这两句诗,恰似他们人生的注脚——一个求功业于沙场,一个悟大道于苍穹。
高适(704-765)生于渤海蓨县(今河北景县),虽是北齐皇室后裔,但家道中落。二十岁西游长安求仕失败,遂定居宋城(今河南商丘)耕读,自称“渔樵孟诸野,一别二十年”。
岑参(715-770)则出身真正的宰相世家:曾祖岑文本、伯祖岑长倩、堂伯岑羲皆官至宰相。但因岑羲参与政变被诛,家族骤衰。他幼年丧父,随兄苦读,立誓“云霄坐致,青紫俯拾”。
当高适在梁宋之地蹉跎岁月时(720-730年),岑参正隐居嵩山读书(725-730年)。两颗未来的边塞诗巨星,此刻都在等待命运的召唤。
天宝三载的梁园(处今河南商丘),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星群在此交汇。被“赐金放还”的李白、壮游天下的杜甫,与本地东道主高适相聚于此。而刚中进士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岑参,也因省亲加入这场盛会。
四人纵猎孟渚泽,酣饮吹台楼。杜甫晚年深情回忆:“昔者与高李,晚登单父台”(《昔游》)。但此时高适与岑参的诗风已见分野:
高适作《古大梁行》悲叹“侠客犹传朱亥名,行人尚识夷门道”,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;
岑参则写《梁园歌》畅想“平台为客忧思多,对酒遂作梁园歌”,尽显浪漫情怀。
后来,高适和岑参都走上了出塞的功名路。高适:河西幕府的务实之路749年:经张九皋举荐,46岁的高适入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。
真实边塞体验:他亲历祁连城戍守,目睹战士“相看白刃血纷纷,死节从来岂顾勋”(《燕歌行》)。
诗风巨变:从早期《别董大》的豪迈,转向《塞上听笛》的苍凉:“雪净胡天牧马还,月明羌笛戍楼间”。
岑参:安西庭州的奇幻之旅749年:34岁的岑参首次出塞,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。
奇幻边塞书写:他以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,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瑰丽想象,重塑西域景观。
第二次出塞(754年):随封常清赴北庭都护府,成就创作巅峰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成为边塞诗最经典的意象。
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(755年),彻底改变二人命运:
高适迎势而起:献策玄宗获赏识,任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李璘。后因蜀中叛乱,任剑南节度使镇守成都。
岑参坎坷南迁:率军东归却遭贬谪,任虢州长史等闲职。宝应元年(762年)才因杜鸿渐举荐,任关西节度判官。
765年正月,历史迎来戏剧性一幕:高适任剑南节度使镇守成都,而岑参被任命为嘉州刺史(今四川乐山),成为高适的下属。
两位边塞诗巨匠在蜀中重逢,却因地位悬殊再无唱和。岑参《赴犍为经龙阁道》写道:“侧径转青壁,危梁透沧波”,道尽行路之难;而高适正为吐蕃入侵焦头烂额,同年十二月病逝长安。
岑参未能送别老友。他继续漂泊蜀中,770年卒于成都客舍。而他们的诗作,早已奠定盛唐边塞诗的双峰格局:
高适的诗笔始终聚焦于战争的真实代价与战士的苦难,在《燕歌行》中以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”的强烈对比,揭露军中的阶级矛盾;而岑参则倾心于描绘边塞的奇幻风光与英雄豪情,在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以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瑰丽想象,重塑了苦寒之地的浪漫意象。
二人的诗学差异更深体现在意象选择上:高适笔下多见“白骨”“羌笛”“风雪”等沉重意象,着力渲染“大漠穷秋塞草腓,孤城落日斗兵稀”的苍凉悲慨;岑参却痴迷于“火山”“热海”“梨花”等奇特意象,纵情书写“火山五月火云厚,千里飞鸟不敢来”的异域奇观。这种差异被明代胡震亨在《唐音癸签》精准概括为“高适诗尚质主理,岑参诗尚巧主景”——一个以理性洞察边塞本质,一个以瑰丽描绘边塞表象。尽管诗风迥异,他们却共同拓展了边塞诗的深度与广度,成为盛唐气象中最雄浑的双声部。
如今,诗人已去,当我们并读《燕歌行》与《白雪歌》,却仿佛看见两位诗人跨马并立:
一个指着雪地尸骨说:“铁衣远戍辛勤久,玉箸应啼别离后”;一个望着漫天飞雪笑:“轮台东门送君去,去时雪满天山路”。
他们用截然不同的诗笔,共同书写了盛唐最雄浑的交响。而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,或许真有过这样一个瞬间——高适放下军报叹道:“嘉州之诗,真得边塞三昧”;岑参搁笔笑答:“仲武兄《燕歌行》二十韵,字字皆溅血泪也”。
双星虽逝,诗卷长明。那些浸透血与火的诗句,至今仍在告诉我们:什么是盛唐气象,什么是诗人肝胆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开户流程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