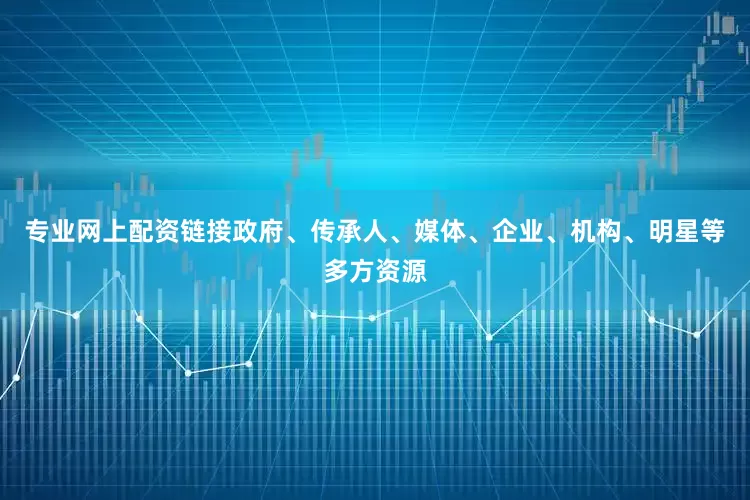衡阳的暮春三月,湘江水雾迷蒙。两位中年文士在渡口久久伫立,衣袂被江风掀起又落下。其中一人忽然提笔疾书:“皇恩若许归田去,晚岁当为邻舍翁”。写罢掷笔,两人相拥恸哭——他们知道,此去一别,今生恐难再见。
这位写诗的人是柳宗元,与他相拥的是刘禹锡。史书将他们并称为“刘柳”,却少有人知,这对大唐最悲情的知己,用二十六年谱写了一段超越生死的文坛绝唱。
一、金榜同题名:长安城里的理想之光
贞元九年(793年)的长安放榜日,20岁的柳宗元与21岁的刘禹锡同登进士第。当礼部侍郎念出这两个毗邻的名字时,谁也不会料到,他们的命运将如藤蔓般终生缠绕。
初入仕途的岁月里,两人同在御史台任职。柳宗元评刘禹锡“才高学富”,刘禹锡赞柳宗元“操行修洁”。志趣相投的他们与吕温、韩泰等人常在僧坊谈经论道,被时人称为“嘉祐四友”。
政治理想在永贞元年(805年)化作惊雷。新即位的唐顺宗启用王叔文推行改革,刘柳二人作为核心幕僚,以雷霆手段打击宦官、废除宫市、减免赋税。当诏书从翰林院雪片般飞出时,他们并肩站在大明宫阶前,眼中映着盛世的曙光。
秋风未起时大厦已倾。宦官集团联合藩镇反扑,改革仅持续百余日便告失败。深秋的霜降日,两道贬谪令同时落下:柳宗元贬邵州司马,刘禹锡贬连州司马。离京途中加贬诏书再至——柳宗元改永州司马,刘禹锡改朗州司马。两只鸿雁从此坠入南方的瘴疠之地。
二、谪路双行影:二十年贬途中的生死相扶
南谪路上,书信成为他们穿越千山万水的舟楫。柳宗元在永州写就《天说》,论证“元气为宇宙本原”;刘禹锡在朗州回赠《天论》三篇,补充“万物皆在矛盾中运动”。哲学思想的碰撞,竟成了寒夜里的薪火。
书法艺术也在纸墨间流转。柳宗元寄给刘禹锡的张衡《西京赋》章草墨迹未干,附诗调侃:“劝君火急添功用,趁取当时二妙声”。刘禹锡展卷笑答:“近来渐有临池兴,为报元常欲抗行”——以书圣钟繇(字元常)喻挚友,自己甘居次席。
元和十年(815年)的春日,长安玄都观的桃花灼灼如血。刚奉诏返京的刘禹锡提笔写下“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”,讥刺新贵如灼灼桃花般转瞬即逝。这首《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》激怒权贵,二人再贬的命运已成定局。
当诏书宣告刘禹锡贬播州(今贵州遵义)、柳宗元贬柳州时,柳宗元突然失声痛哭:“播州非人所居!梦得(刘禹锡字梦得)有八十老母,岂能随行?”他连夜写就奏疏,愿以柳州换播州——“虽重得罪,死不恨!”。这份奏章震动朝野,连唐宪宗都为之动容,最终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。
三、湘水断肠处:衡阳诀别的诗笺泪
南下的官船沿湘江漂流,两位知己在舟中对饮。过襄阳宜城驿时,他们同谒战国名士淳于髡墓。刘禹锡泼酒吟诗:“我有一石酒,置君坟树前”,柳宗元即兴唱和:“刘伶今日意,异代是同声”。醇酒伴着戏谑,暂时冲淡了贬谪的阴云。
行至衡阳,分路时刻终至。柳宗元需溯湘江赴柳州,刘禹锡则越五岭往连州。渡口柳枝低垂,柳宗元将诗笺塞入挚友手中:
“二十年来万事同,今朝歧路忽西东。”
“今朝不用临河别,垂泪千行便濯缨。”
刘禹锡展开《重别梦得》,读到“晚岁当为邻舍翁”时双手颤抖,含泪酬答:
“归目并随回雁尽,愁肠正遇断猿时。”
“桂江东过连山下,相望长吟有所思。”
江风卷起诗稿,几滴墨迹在湘水中晕开,如离人泪痕。两人不会想到,这竟是此生最后一面。
四、遗稿托孤人:柳州烟雨中的生死约
柳州城头的四年,柳宗元在瘴气中呕心沥血:释奴婢、凿水井、兴学堂。元和十四年(819年)深秋,肺疾缠身的他预感大限将至,将书信与书稿托付老仆:“遗草累故人...”喘息中写下的,是给刘禹锡的绝笔。
此时刘禹锡正扶母柩北归,行至衡阳忽闻噩耗。当年分手的渡口依旧,故人却已永诀。他“惊号大叫,如得狂病”,朝着柳州方向长跪不起。含泪写下《重至衡阳伤柳仪曹》:“千里江蓠春,故人今不见”。
赶至柳州,只见灵堂素幡。柳宗元四个幼子跪在棺前,长子周六仅四岁。刘禹锡颤抖着手展开遗稿——44卷诗文,字字皆心血。他当即立誓:为亡友编全集,育遗孤如己出。
此后岁月,刘禹锡在洛阳陋室埋首校雠。每当整理到《江雪》《捕蛇者说》等篇,便想起当年永州书信往来时柳宗元的笑谈。编成《河东先生集》那日,他携书稿至柳宗元墓前酹酒:“子厚,文字传矣!”抚养周六成人后,又为其操办婚事。当新人叩拜时,刘禹锡恍见故友含笑的身影。
大和二年(828年),白发苍苍的刘禹锡路经永州愚溪。当年柳宗元在此写下的《愚溪诗序》墨香犹在,溪畔草堂却已荒芜。提笔作《伤愚溪三首》,其中“纵有邻人解吹笛,山阳旧侣更谁过”化用嵇康亡后向秀作《思旧赋》的典故,字字泣血。
柳宗元病殁二十三年后,刘禹锡在洛阳走完人生路。后人将他归葬荥阳,与柳州孤坟隔山相望。这对知己终未能实现“邻舍翁”的约定,但他们的精神早已在文字中永恒交融。
翻开发黄的《河东先生集》,卷首刘禹锡亲撰的序言墨迹如新:“凡子厚(柳宗元字子厚)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,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”。他毕生守护的不仅是亡友的文集,更是**中国文人间最珍贵的道义——政见可争,生死不负**。
当我们在柳江边吟诵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,在连州古城抚摸刘禹锡手植的橘树,恍惚可见两个清瘦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:一人执笔疾书,一人捧卷校字;衡阳的雨丝落在他们肩头,却浇不灭眼中灼灼的光芒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开户流程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